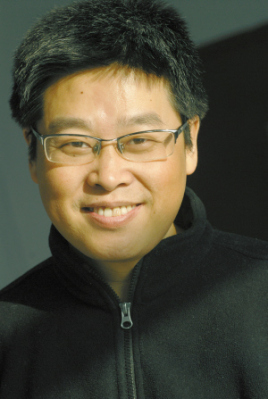1。
冬天的上午,
我在凌源集市卖布。
一朵大红的纸花把我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改朝换代战争大戏的群众演员。
我骑在我的毛驴上,
我亲手织的土布也已成为光荣的军需品。
一个邋遢的军官说,
你会得到十倍于这些的洋布。
我没有注意围观者不怀好意的欢呼只低头看见纸花边缘还未修饰的毛刺儿还有我的毛驴,
它示威似地发出滑稽的哭声。
2。
当时,
我已经31岁,
虽然比我一个后来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儿子相比还小了两岁,
但我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比他丰富,
他的智慧和诡计大多来自于荒唐的书本——让他碰壁的指南或手册。
我想活着,
即使挨饿;
我想回家,
即使除了土墙和一辆我自己制造的木轮车。
我的长子12岁,
他已经是田野的主人;
我的第二任妻子21岁,
她是家庭的灵魂。
3。
我回到了家中,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没有血性的逃兵。
后来,
我的四子向我竖起大拇哥:
爸爸,
原来你就是海明威笔下的英雄。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只知道生命只有一次,
它让我胆子小,
不适合在人群的黑暗中出没。
当我重新开始我日出而作的生活,
当我忘记我深爱的毛驴变成了哪一个可怜虫盘碟中的食物一把刺刀把我重新拖入战争耀眼的旋涡。
4。
和红花的文明相比,
刺刀仿佛野兽但它坦率——这让我更早更明智地放弃幻想的烧酒。
所以没等到新兵营我就开始设计逃跑的计划,
这使我的表情和那些十五六岁的后生看上去是那么不同。
长官没有让我去当伙夫,
虽然这个职位更适合我稳重的性格;
也没有让我当马夫,
虽然我养育毛驴的技术是如此成熟我只是悲伤的步兵,
需要时献出自家的头颅。
5。
这一次摆脱战争是如此不顺,
换句话说我根本无法发现它的缝隙。
而且我多次目睹那些被抓回来的英雄的下场——在土坑里等待活埋,
这让我胆战心惊:
在梦里,
不是被子弹击中,
就是被黄沙覆盖在深邃的地层。
我还梦见了一只手,
从土里伸出,
喊着我幼时的贱名。
我读过私塾,
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白狼河北音书断。
白狼河,
我童年的免费游泳池,
今天它就是妖精煮唐僧的大锅!
6。
在梦想逃跑的日子里,
我的旅行地图在山炮嘶哑的伴奏声中变得模糊。
我不知自己是在什么鬼地方,
我的伙伴一到驻地,
就找肉类食物包括那些美丽的女人——他们这些坏蛋因为不知明天的命运而抢夺暂时的愚蠢的欢乐。
我拔出军用腰带上的旱烟袋,
这是我勉强可以找到的享受。
偶尔还能放上点儿烟膏——从罂粟中提炼这玩意儿,
我可是内行,
顺便安慰一下越来越疼的肩膀,
越来越远的家乡。
7。
看不见对面的敌人,
看不见即将出现的尸体。
漫山遍野的军队,
坦克、卡车和时代的喧嚣。
我握着步枪,
心里嘀咕:
今天我是否像昨天一样幸运,
躲过阎王——死神温柔的拥抱?
我也反复想过子弹穿过我的刹那,
我是毫无知觉死去还是疼得一塌糊涂?
最好是当时就死——那些垂死挣扎的人用隔世的祝福请求我补上一枪。
20年后,
一起种菜的老罗讲起这著名的战役我听着,
他对面的枪中有我一支却始终没讲。
8。
夜晚来临,
长官搜走褴褛的上衣和裤子。
为遏制逃兵指数的增长,
他们已毫无顾忌地使出让人嘲笑的吃奶的力量。
我打着鼾声,
眼望露天里的星星,
我没有奢望神的救助也不指望自己能够长出什么翅膀,
我只是等待着一个不经意间暴露出的机会,
只要有一个哪怕成功率很小的机会,
我也会牢牢地抓住不放。
我在石头下藏了一身便装,
它旁边就是一丛密实的高粱。
我不会把枪拿走,
那会激怒暴力的毒肠。
9。
翻山越岭,
榛丛草莽,
回故乡之路多么的甜蜜,
我咀嚼自己骄傲的心灵。
回头看去,
战争的阴影被我甩到爪哇国的边疆。
但我不敢掉以轻心,
危险随时都会现出它狰狞的面孔,
张牙舞爪,
让人防不胜防。
游击队的要求当然不算过分,
保卫你我的家嘛。
但我还是客气地回绝了:
我更适合做个农夫安静地守着几亩薄田,
几间破烂的草房研究种花的手艺,
就够我消耗一生的才华。